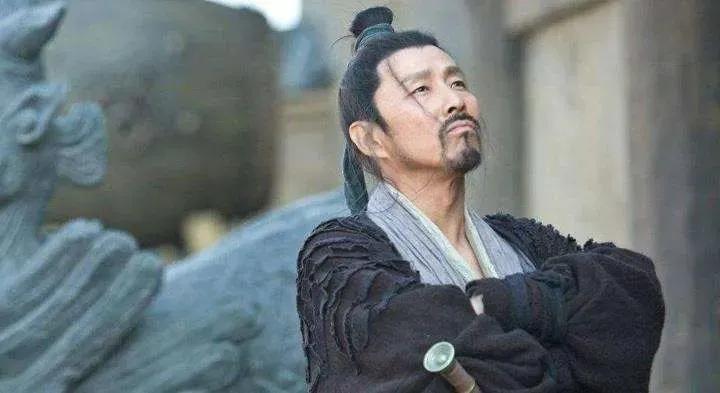早在20世纪40年代,牛津大学的中国历史教授霍莫率先提出,骊靬居民是参加卡莱之战的罗马俘虏后代。稍后,这个学说被美国汉学家德效骞所继承,断定骊靬人祖上参加过郅支城之战,向汉朝军队展示类似古罗马龟甲阵的鱼鳞队形。
正是通过两人的孜孜不倦,假说的细节日趋完善,甚至形成某种闭环:甘露元年(前53年),克拉苏的罗马军队在卡莱之战中惨败,许多士兵被帕提亚人俘虏。帕提亚人将罗马俘虏安置在东部前线,其中一些勇者相约逃跑,流落到中亚充当佣兵。汉朝军队西征郅支城,击败罗马士兵,将他们二次俘虏到河西走廊。
在那个许多史料尚未被整理、缺乏科技支持,又很难展开实地考察的特殊岁月,类似的奇谈怪论不胜枚举。骊靬罗马人不过是芸芸众生的冰山一角。纵使有李约瑟的《中国科技史》、安田朴的《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和布瓦努尔的《丝绸之路》支持,依然只是上不了台面的非主流论断。
然而,事情在20世纪末发生突变。1989年,作为兰州大学外籍教师的澳大利亚人哈里斯,突然向报社撰文,声称已找到西汉安置罗马战俘的城市。随即与同校的俄语教师瓦谢里金,以及历史系教师陈正义等人联手,四处宣扬自己的伟大发现。
那么,是否有切实证据,能够证明骊靬罗马人假说?很不幸,至今为止是一条都没有!甚至每一条潜在依据背后,皆是能道破谣言的反面案例!

首先是在古罗马历史记载方面,有关于卡莱之战前因后果和损耗情况的详细赘述。克拉苏率领的43000大军中,光阵亡、非战斗减员数量就高达20000人,另有10000左右被俘。余下残部要么成建制撤退,要么以各自的小单位分头突围,基本逃到叙利亚的罗马控制区内。
此后,这些罗马俘虏被安排到呼罗珊地区戍边。此地距离郅支城所在塔拉兹还相距甚远,沿途又分布着大量同帕提亚人不对付的游牧蛮族,根本不可能吸引俘虏前去冒险。何况罗马人要逃出生天,必然优先选择家乡所在的西方,而不是越来越遥远的陌生东方。
其次,汉朝方面的历史记载,同样否认骊靬罗马人假说。譬如作为风波起源地的郅支城,原本并无固定城寨,直到北匈奴流亡者抵达才草草建城。如此粗糙的小型堡垒,如何吸引习惯于城市生活的罗马士兵?至于所谓的“夹门鱼鳞阵”,不过是针对密集排列的修辞手法,在世界各地都有能对号入座的备选。

陈汤
另一方面,汉史中的骊靬建立日期为甘露四年(前50年),距离陈汤西征的建昭三年(前36年)有较长空窗期。当初为郅支单于奋战的匈奴和其他胡族,总数不超过4000人,其中仅1000人战死。余下皆被汉军分配给西域诸邦,根本没什么大规模押解回师记录。
正因如此,国内外学界早就质疑甘肃罗马后裔假说:1962年的美国学者斯凯勒就曾指出,古代中国称呼罗马为“大秦”,而非小众的“骊靬”。1967年的台湾学者杨希枚更是批判假设本身“几无一是处”!
当然,最为有利的证据来自分子人类学:根据2007年发表的《人类遗传学杂志》,骊靬本地居民的Y染色体不但与欧洲较远,反倒是和三个汉族人群极为接近。两年后发表的《中国西北骊靬人起源的线粒体遗传多态性研究》也表明,骊靬居民的线粒体DNA与中国汉族亲缘关系最近,而与欧洲人或中亚人的亲缘关系较远。


![中国历史基本上中原不内乱,游牧就只有挨打的份[6]](http://image.uczzd.cn/422124218612007233.jpg?id=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