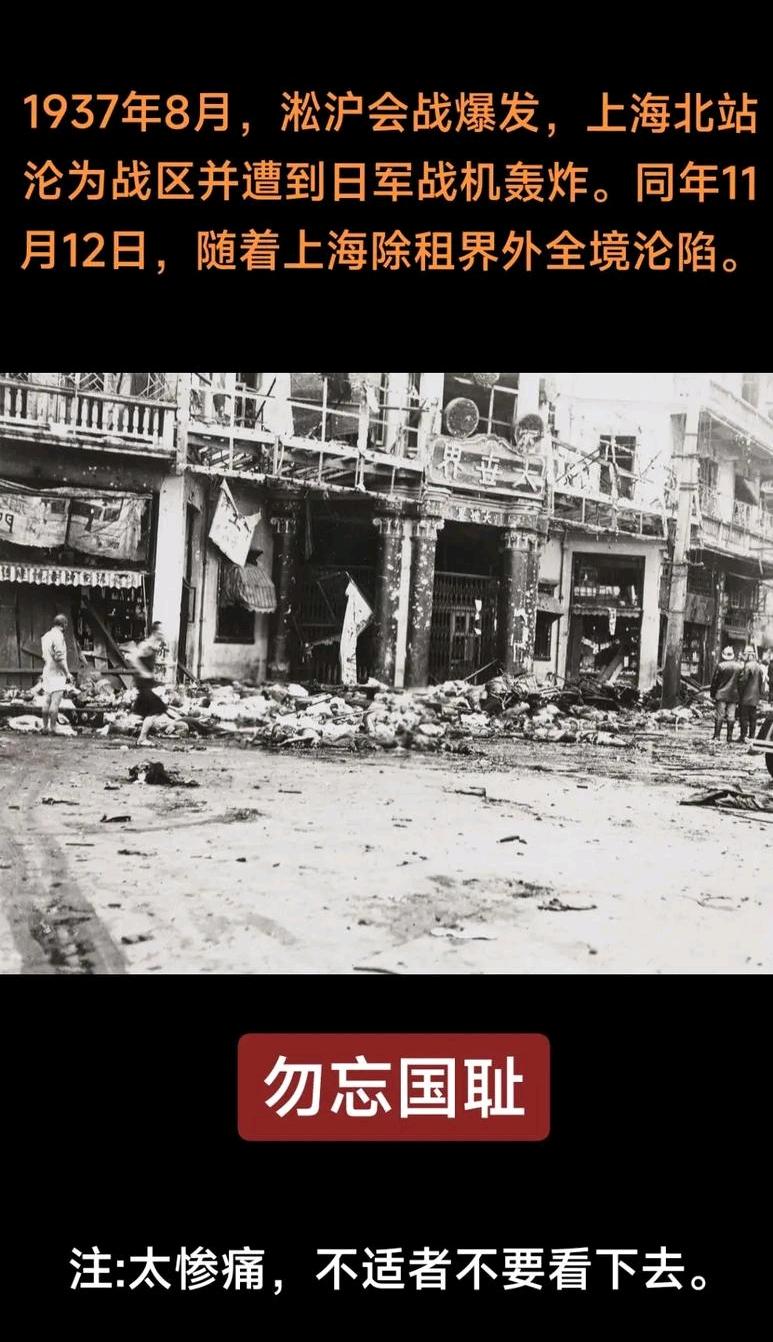1945年3月20日深夜,硫磺岛的海风依旧猛烈,地下坑道里却闷得几乎透不过气来。湿冷的空气中混杂着血腥味、火药味,还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腐臭气息。有人轻声嘀咕了一句:“这样下去,还能撑几天?”没有人回答,因为人人心里都明白,这个问题已经毫无意义。
这一晚,硫磺岛战役已经打到尾声。自2月19日美军登陆以来,不到一个月,岛上原本约2.3万名日军守备部队,已经有2.2万多人阵亡,剩下的不过一千五六百人,大多蜷缩在地下壕沟和坑道里,靠干粮残渣和污浊的积水硬撑。岛上地面早被美军彻底控制,11万美军兵力、舰炮、航空兵轮番上阵,日军只能像被逼到角落的老鼠,缩在黑暗里动弹不得。
从这一天开始,硫磺岛上的日军面对的已不再只是战斗的失败,而是一个更残酷的问题:是等死,还是自己动手去死。
有意思的是,当时绝大多数活下来的日军,并不是真心“想死”。他们中的很多人,哪怕已经明白大势已去,心底仍旧在挣扎,仍旧想要抓住那一点点虚无缥缈的“活路”。正是在这种极度扭曲的绝望之下,一连串看似荒唐,却又真实发生的自救与自杀场景,开始在硫磺岛的坑道里轮番上演。
被围困在地下的人:饥饿、幻想与“逃生计划”战斗打到3月中旬,硫磺岛地面上几乎看不到完整的日军阵地。折钵山、机场附近、海滩边缘,到处是炮弹坑和焦黑的残骸。日军留下的弹药被大量消耗,补给早已中断,剩下的残兵只好退进早就挖好的地下要塞。

这些地下坑道,是栗林忠道在战前精心布置的,全岛纵横交错,最长的坑道能延伸到几十米深。战争初期,这些坑道是日军的“依仗”,能在美军强大火力下保存实力;但打到后期,坑道在某种意义上反而成了困住他们的牢笼。
坑道里光线昏暗,灯油耗尽后,只能靠偶尔点燃的蜡烛或火柴照亮一小片空间。士兵们挤在一起,背靠着潮湿的泥壁,衣服上全是血迹和泥土。很多人已经好几天没有吃到像样的东西,喉咙干得冒火,喝的多是带着泥沙和血水味道的积水。
在这样的环境下,“活下去”反而成了一种折磨。不得不说,人一旦被逼到了绝境,想象力往往比平时更丰富。
有一天夜里,有人突然提出一个主意:趁夜色掩护,沿着峭壁翻到海边,跳进海里,游回日本本土。他们嘴里念叨着的,是“回去告诉大家硫磺岛的情况”,但更真实的想法,其实只有四个字——逃离此地。
从硫磺岛到日本本土,直线距离大约1250公里。这个数字,在平时稍一算就知道不可能,但在地下坑道里,这些人却越想越觉得可行。有人说,不必直接游回日本,可以先游到周围的小岛,比如约270公里外的小笠原群岛,或者北面80公里的北硫磺岛、南面60公里的南硫磺岛,只要能离开这个“地狱岛”,就算趴在竹筏上漂也行。
有的士兵甚至在昏暗的坑道里画起简陋的“海图”,手指在泥土上比划,嘴里反复念叨:“从这里出发,顺着洋流,迟早能碰到陆地。”

试想一下,在弹药匮乏、食物断绝的情况下,这些所谓“计划”,更像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可是对一群已经被困疯了的人来说,这些想象却成了维持精神不崩溃的支撑。
那几天,少数有行动能力的士兵开始悄悄往海边摸索。他们在海岸线附近找来木板、竹竿、电线杆,扎成简陋的筏子,准备拼一次。
“跳海”这条路:从希望到绝望的封死3月20日晚,大约八点钟,坑道口出现了一阵窸窣的动静。三十名日军士兵陆续背起简单行囊,准备离开坑道,向海边进发。这支小队中,有些人已经饿得眼圈深陷,有些人则显得异常亢奋,仿佛找到了出路。
海军一等兵金井以及另一名一等兵大曲劝他们不要冒险。金井把人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外海有巡逻的美军舰艇,还有鲨鱼,这样出去就是送命。”对方却摆摆手,说在海边已经扎好了筏子,可以乘着洋流往日本方向漂,绝不愿再缩在坑道里等死。
对这三十个人而言,留在坑道里意味着慢慢被饿死、渴死,或被炸死,跳海则像是一种“主动选择命运”的方式。他们宁愿在波涛里搏一回,也不愿在黑暗中等死。不得不说,这种心态在极端环境下并不难理解。

然而事实远比他们想象的更残酷。
硫磺岛周边海域因为长期有海战和舰炮轰击,海面上常常漂浮着尸体和残骸,这种情况下,大量鲨鱼被吸引而来,几乎成群游弋。美军有记录提到,战斗期间,这一带海域“异常活跃”。
那天夜里,三十名士兵分批从暗处摸到海边,有人抓住电线杆,有人坐在用竹竿扎成的筏子上,借着微弱月光,向黑暗的海域游去。有的嘴里还在念叨:“只要离开这个岛,就还有机会。”
结果很快显露出来。部分人刚下海不久,就被美军巡逻队发现,机枪在夜色中喷出火舌,几个黑影应声翻在浪里。还有一些人,筏子被浪头掀翻,没来得及挣扎,就被巨浪吞没。
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前也有个别日本兵尝试从海边跳入海中“游走”,却在当天夜里就被海浪拍回原来的岸边,浑身是伤,只得爬回坑道。
三十人的“逃亡”行动以全员死亡告终。无论是被美军火力击中,还是被巨浪卷走,又或者落入鲨鱼口中,都没有一个活着回来。

这件事在坑道里传开之后,任何有心再谈“跳海逃生”的人都被现实压得说不出话来。那条曾经被幻想为“通往希望的海路”,就此彻底封死。
值得一提的是,对当时那些残兵来说,被海浪卷走或者被鲨鱼撕咬致死,本身就带着一种特殊的恐惧感。有人宁可选择在坑道里结束自己的生命,也不想在深不见底的大海里做一具无名尸体。
从这天晚上起,很多人心里的“活路”彻底熄灭。坑道中弥漫的不再是勉强支撑的希望,而是逼近的死亡感。这时,自杀的念头开始在更多人心中发芽,并且快速蔓延。
绝望中的选择:手榴弹、刺刀与“互相了断”美军的作战方式很明确:用绝对优势火力压制,逐步清理地面工事,同时封锁补给和出路。对于藏在坑道里的日军,他们并不急于一股脑冲进去拼刺刀,而是采用爆破、火焰喷射器、手榴弹投掷等手段,将任何可能的抵抗力量一点一点磨掉。
这意味着,藏在地下的日军看似一时没被“正面消灭”,实际上却被逼入一个几乎没有出路的慢性死亡环境。美军在战术上并没有直接“要求”日军自杀,但以战场态势来说,留给日军的选择已经非常有限:要么出来投降,要么留在坑道里饿死、被炸死,或者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

栗林忠道
在日本军队长期灌输的军纪和观念里,“投降”几乎等同于奇耻大辱。尤其是在硫磺岛守备队司令官栗林忠道的严格要求下,“不准轻易投降”“宁死不屈”“玉碎”等口号,从战前就反复灌输给每一个士兵。
火力优势明显的美军逼在外面,自身的武器、补给又所剩无几,一些日军士兵的心理开始发生变化:既然投降被视为耻辱,那就只能选择自己动手,去完成所谓“光荣的死亡”。
然而在现实中,自杀远没有口号里说得那样“干脆利落”。
在硫磺岛的地下坑道里,自杀的方式大致有几种:手榴弹、刺刀剖腹、冲出战壕故意暴露在美军火力下,还有极端的“互相捅刺”。
手榴弹本是给敌人用的,现在却被用在自己身上。许多士兵在动手前,其实并不完全懂得自杀的“诀窍”。理论上,要用手榴弹结束生命,拉开引线后,必须将手榴弹紧紧按在胸口或腹部,用力抱住,爆炸时才能造成致命伤。如果只是握在手里,很多时候只会炸断手腕、炸掉五官,却不足以立刻致死。
坑道中有不少新兵,对这些细节并不完全了解。拉响手榴弹后,他们条件反射般把手伸得远远的,下一刻,伴随着一声巨响,手脚被炸断,脸也被炸得血肉模糊,却还残喘着。于是坑道里时常能看到这样一幕:一个人倒在地上,断手断脚,口中发出撕裂喉咙的惨叫,半天死不掉。

在这种情况下,旁边的战友往往不得不做一件极其残酷的事。有人咬着牙端起步枪补一枪,有人握着刺刀,硬着头皮给濒死的同伴“了断”。这种场景,对施刀的人来说,同样是一种精神上的折磨。
与此同时,由于弹药紧缺,每两三名士兵才配有一颗手榴弹,这也导致了另一种惨烈景象的出现:几个人抱着同一枚手榴弹,一起拉响,引爆瞬间,有的人当场死亡,有的人却只是重伤。缺乏后续处理的情况下,那些重伤者只能在坑道里慢慢痛死。
地下坑道在这一阶段几乎变成了一座活生生的“集体自杀地”。原本用来对抗敌人的堡垒,逐渐成了堆满自己人尸体的坟墓。
刺刀剖腹也是当时许多士兵被灌输的“武士道式”死法。理论上,这种方式被包装成“勇敢”“决绝”的象征,但真正拿起刺刀对准自己腹部时,多数人会在那一瞬间犹豫。刀尖刺入皮肉时的剧痛,不是简简单单一句“为国捐躯”就能压下去的。
有的士兵狠下心刺了一刀,却没敢拉开伤口,结果既没能立刻死去,又疼得浑身发抖。旁边人看了,有的帮忙“补刀”,有的则干脆不敢靠近,只能侧头避开视线。

在这些惨烈场景中,出现了一种更极端的方式:两个士兵背对背或面对面,各自握着刺刀,将刀尖对准对方的胸口或腹部,约定好一起用力刺下去。这样一来,至少不用自己对自己下手。
金井后来回忆,有一次看到两个士兵相互对视,脸上的表情既悲哀又决绝,其中一个低声说:“这样,谁都不用再犹豫了。”话音刚落,两人同时发力,刺刀没入对方身体,血一下子涌出来。可即便这样,也不是每一次都能立刻致命,往往还伴随着长时间的挣扎和呻吟。
还有一些人则选择了看似“简单”的办法:趁美军火力相对集中的时刻,大喊着从坑道里冲出去,故意暴露在机枪和火炮的射程之下。他们冲出掩体,甚至有人刻意站在高处,直面敌方射击。结果可想而知——几乎没有人在这样的“冲锋”中存活。
这种行为不完全是战术意义上的反冲击,更像是一种“借敌人之手”结束生命的极端方式。对这些人而言,被美军子弹打成筛子,也比在坑道里慢慢饿死、渴死,或者在手榴弹残爆中痛苦嚎叫要“干脆”得多。
在这段时间里,自杀人数难以精确统计,有说法认为至少在三五百人以上,而且很可能不止这个数字。坑道越往深处走,越能看到散落在角落里的尸体,有的全身焦黑,有的仅仅是胸口、腹部留下一个致命伤口,还有的缺胳膊少腿,已经看不清原貌。

不得不说,这些自杀方式在任何角度看,都谈不上所谓“体面”。所谓“光荣玉碎”的包装,在实际战况面前,变成了极其残酷的肉体摧残。
活下来的少数人:投降与迟到的清醒在许多日本兵看来,那些没有自杀的人是“懦夫”“不够忠诚”。这种看法在当时的军队氛围中相当普遍。有人对不肯自尽的同伴露出轻蔑的眼神,有人嘀咕“连死都不敢,还算什么军人”。
通信兵秋草就是被这类眼神“围攻”的一员。他身为通信兵,平时没有配发步枪和手榴弹,手边只有一把在战壕里捡来的旧刺刀。刀身锈迹斑斑,锋利程度都成问题。秋草看着那把刺刀,总觉得用这种破刀结束自己的生命,实在说不上什么“体面”。他不止一次在坑道里劝人:“再等等,看能不能有别的办法。”金井的态度也类似,两人都觉得,盲目自杀没有任何意义。但在当时被“玉碎”思想裹挟的环境里,他们的劝说几乎没人愿意听。
栗林忠道在自尽前曾向部下提出过一个极高的要求——“以一杀十”。意思是,每名日军士兵在战死前,至少要拉十个美军陪葬,这样才算没有辜负“天皇的军队”这块牌子。这种说法既是不切实际的战术幻想,也是对下级的一种精神捆绑。
在硫磺岛后期战况下,大部分日军士兵连基本的弹药都难以保证,更不用提“以一杀十”这种目标。很多人连保护自己的能力都丧失了,更遑论再多杀敌人。

战局发展到3月下旬,硫磺岛战役事实上已经接近尾声。美军控制了所有关键地带,日军组织的有规模反击基本停止。残存在坑道里的部队成了意义不大的零星抵抗。
金井、秋草等少数人在目睹一批批战友用各种方式结束生命后,逐渐意识到,一味守在坑道里,只剩下两条路:要么被炸死,要么自杀。他们反复权衡后,开始萌生另一个念头——走出坑道,向美军缴械。
对当时的他们来说,这一步并不容易。需要跨过的不只是枪口,还有长期灌输的观念。有人犹豫着问:“出去之后,会不会被当场打死?”也有人忧虑:“回国之后,家人会怎么看?”
即便如此,仍有几百人最终做出了选择。他们在某个时间点放下手上的刺刀和残存的弹药,举起双手,走出黑暗的坑道,迎向美军阵地。
值得注意的是,美军在硫磺岛战役中,对于主动投降的日军俘虏,整体上还是按照战俘惯例予以收容,并没有像一些日军事先想象的那样“一律就地处决”。这部分后来成为战后回忆中被反复提及的细节。

战役结束统计时,硫磺岛上约2.3万多名日军士兵中,阵亡人数超过2.2万,仅有一千余人以负伤、投降等方式活了下来。金井和秋草就位列其中。
几十年后,金井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人。回忆起当年在硫磺岛的经历,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硫磺岛是日本兵的地狱。”他坦言,那些年最难以释怀的,不是自己差点死去,而是亲眼目睹那么多同袍在逼仄的坑道里,用种种极端方式结束生命,却连“体面”二字都谈不上。
回看硫磺岛战役,它在军事层面上的意义,已经有大量研究。对美军而言,这是夺取对本土进攻跳板的一场关键战役;对日本而言,则是本土防线被撕开缺口的重要标志之一。

而在冰冷的战损数字之外,那些被困在地下、在绝望中自杀的普通士兵,构成了另一层难以忽视的现实。所谓“逼得我们自杀”的说法,并不是一句简单的抱怨,而是当时综合环境、战略态势、军队观念共同作用下,逼迫许多人走上极端选择的结果。
如果从战场正面看硫磺岛,这是一场伤亡惨烈、火力密集的对峙;若从坑道内部看同一场战役,看到的却是另一种极端——一个在战略上早已失去希望,却仍被要求“战斗到最后一人”的群体,在被围困、被饥饿、被恐惧压垮之后,在黑暗中一步步走向自我毁灭。
这一层残酷,恰恰隐藏在华丽口号和简单数字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