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乔·拜登昨晚表示:“在长达50多年的当选公职生涯中,这是我见过的最糟糕的情形。说实话,我们的民主正处于危险之中……美国不应该是一个充满极端主义和愤怒的地方,而应是一个充满体面和优雅的地方。我们的民主值得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 这句话掷地有声,也带着一丝绝望。熟悉拜登的人都知道,他向来是政坛的“温和派”。五十多年来,他见过水门事件、冷战尾声、9·11恐袭、金融危机、国会山骚乱,但在卸任之后说出“最糟糕的情形”,足见他眼中美国的“病”已深入骨髓。 拜登的政治生涯从1973年正式起步。那一年,年轻的特拉华州参议员在国会宣誓时还带着新婚的光环,却在数月后遭遇家庭悲剧,妻女在车祸中去世。这个从痛苦中爬起来的人,之后一路在国会打拼三十多年,参与无数立法、谈判与外交场合,自诩“见识过人性的全部颜色”。他常说,政治是服务而不是战争。 但进入21世纪后,美国政治越来越像一场永无止境的内战。拜登曾在奥巴马手下当了八年副总统,目睹党派分裂从议会蔓延到社会。那时的争吵还局限于政策——医保、税收、移民。可到2020年代,裂痕已经深入制度本身,谁赢了选举、谁说的是真话,都成了争议。 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山被冲击。拜登在电视上看着人群闯入国会大厅的画面,说那是“我一生中见过对民主最黑暗的一天”。那一刻,美国的自信坍塌。几天后,他宣誓就任总统,口号是“团结国家”。但现实告诉他,撕裂远比想象的深。一个国家如果连事实都不共用,就谈不上团结。 拜登在任期间推过基础设施法案、绿色能源计划,也花大力气恢复国际盟友关系。但在国内,他始终被一种汹涌的“愤怒政治”包围。无论政策成败,民众首先讨论的是立场,而非内容。电视辩论成了表演,网络言论沦为战场,议员不再谈协商,只谈胜负。 到了2024年,美国政治彻底陷入对抗循环。大选前后,关于“民主是否还能运行”的质疑几乎天天出现。拜登频频提醒选民,民主不是理所当然的,它需要被守护。那时很多人还觉得他在渲染恐慌。可到了2025年,拜登卸任数月后这番话响起时,语气变得更沉重——他不再代表任何党派,只是在以一个“老政治人”的身份发出警告。 这番讲话发生在一次公共服务奖的颁奖典礼上。拜登坐在台下,神情疲惫,头发花白。他缓缓起身,话筒前第一句话就是:“我从政五十多年,从未见过如此危险的时刻。”全场安静了几秒。那不是老年人的感叹,而是一个见证者的哀叹。极端主义在美国政治中已不再是边缘词。它有了组织、有了话语权,甚至有了选票。 拜登说的“危险”,指的不只是暴力,而是一种心态——拒绝妥协、拒绝真相、拒绝文明。过去美国人相信规则,相信法院的判决、新闻的报道、选票的结果。如今这些都被质疑,被撕扯。阴谋论比新闻传播得更快,愤怒比理性更能动员。一个原本以宪法自豪的国家,如今在争论宪法是否还有意义。 在讲话中,拜登提到“体面”和“优雅”这两个词。那不是装饰性的词汇,而是美国政治传统的象征。体面,是输赢皆守底线;优雅,是知道克制与尊重。可现在,赢者要碾压,输者要翻盘,舆论场成了比谁更狠的角斗场。拜登说:“如果政治成了复仇的游戏,那我们就不是民主国家。”这话让不少在场人士低头。 拜登也清楚,自己已无实权。说这番话,不是为党派冲锋,而是留下一份清单——总统权力必须受限,国会必须独立运转,司法必须自由裁决,媒体必须监督权力。这四点,是美国政治能维系半个世纪的根。如今,这些根都在动摇。 他的警告既是对外,也是对内。外部世界在观察美国,盟友看它能否维持稳定,对手看它是否会自乱阵脚。而内部民众更在厌倦政治,却又深陷争吵。拜登讲到“我们的民主值得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时,声音略带颤抖。有人说,那像一封留给后辈的遗嘱。 不少评论指出,拜登的这番话,是他政治生涯的总结,也是美国的镜像。一个自诩为“世界民主样板”的国家,如今陷在身份认同和价值撕裂中。拜登这一代人靠协商解决问题,新一代人却靠标签判断敌友。过去议会的妥协被看作“政治智慧”,现在却被骂成“出卖信念”。 拜登口中的“最糟糕”,或许正是这种转变的绝望——当政治失去信任,当民众不再相信制度能纠错,民主的外壳再漂亮,也只是空架子。 美国媒体事后评论,这番讲话的分量,不在内容,而在时机。就在数月前,拜登被诊断出前列腺癌,身体每况愈下。病中再谈民主,语气更像是见证一场漫长衰败。他不是在为个人辩护,而是在替国家做病历记录:这个国家的“病灶”,是愤怒、是仇恨、是对制度的怀疑。 一个国家的危机,不一定来自外部入侵,也可能来自内部信任的坍塌。拜登这一句“我们的民主值得我们不惜一切代价去捍卫”,像是在提醒美国:民主不是自然状态,而是一种持续修复的工程。若人人都以愤怒为荣,那再强的制度,也会慢慢碎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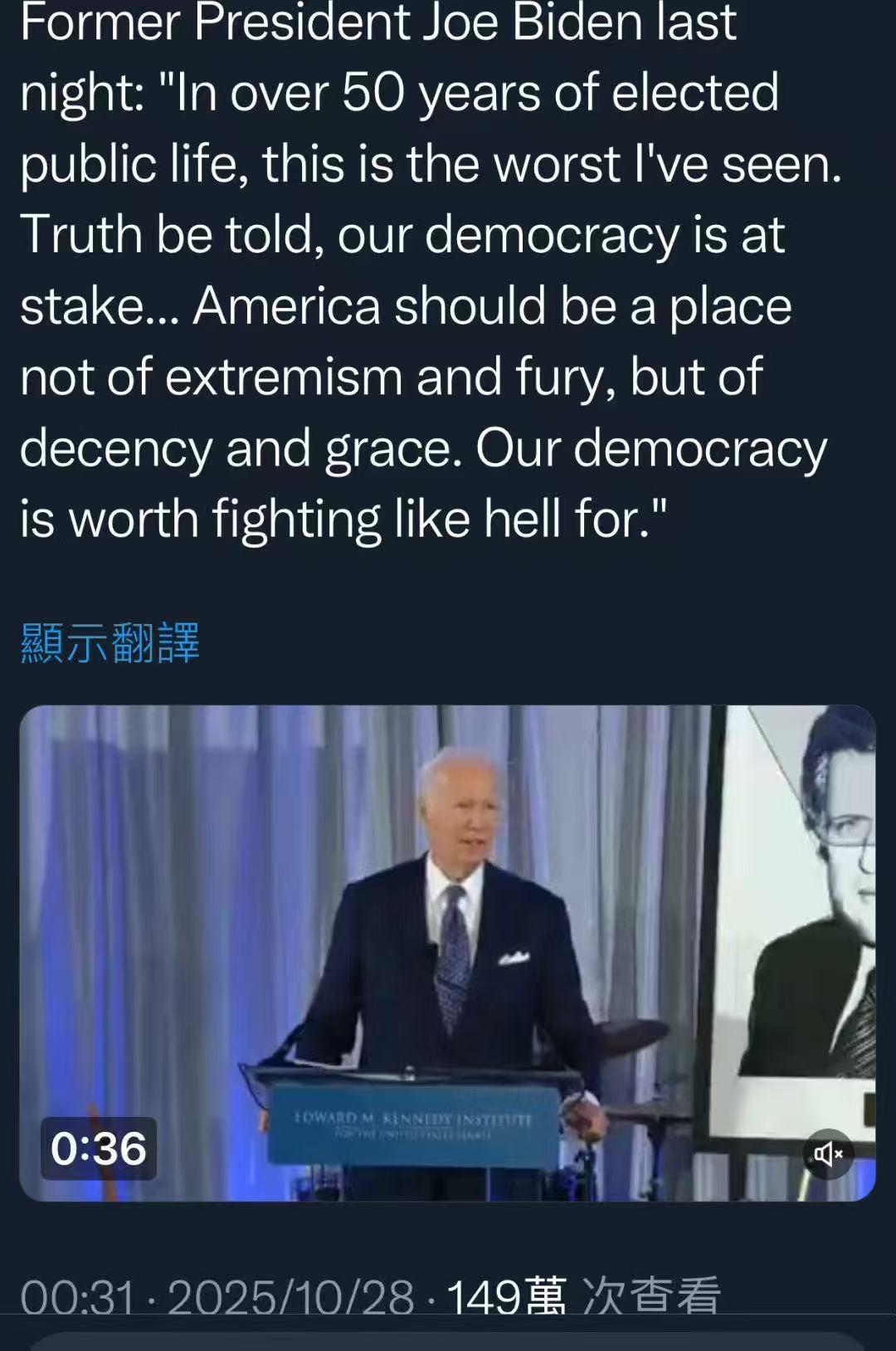
评论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