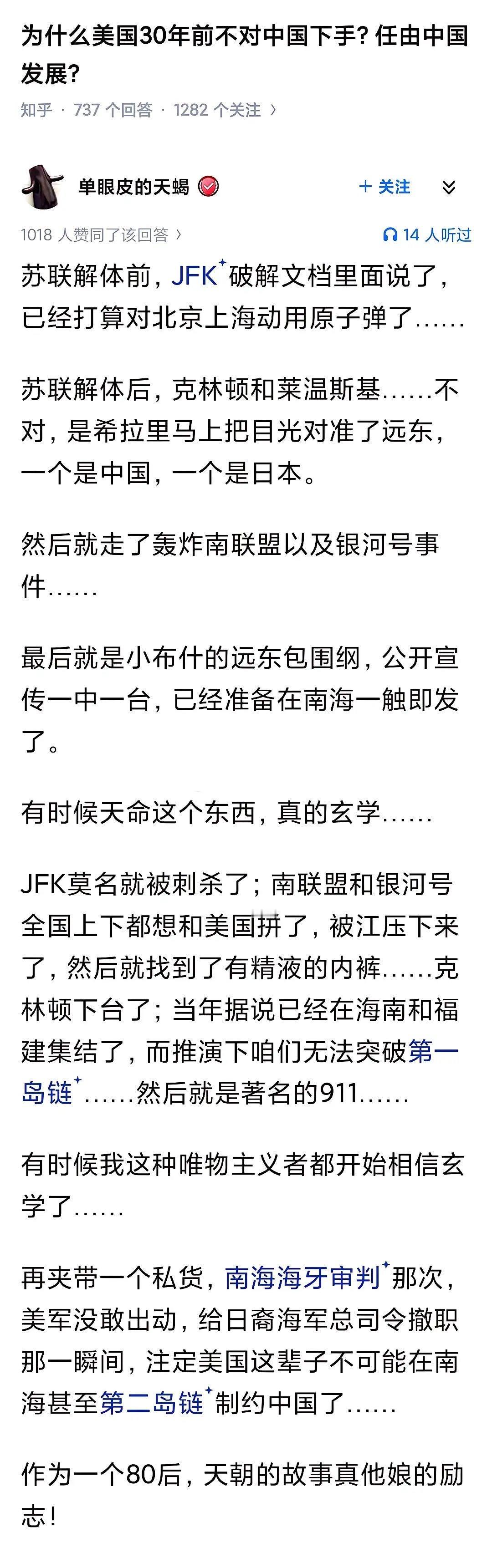1945 年,一个美国大兵喝醉了酒,开车撞死了一个 12 岁的中国小女孩,却只赔 26 美元,李敦白大怒:“一条人命就值这点钱?” 李敦白攥着那几张皱巴巴的美钞,站在巷口,觉得手里的纸片烫得吓人。旁边母亲的哭声像钝刀子,一下下割着周围的空气。他没去美军驻地——去了又能怎样呢?治外法权像一道铁栅栏,隔开了两个世界。 他蹲下身,对那母亲用生硬的中文说:“这钱,您先拿着。”女人只是摇头,手死死抠着地面。李敦白叹了口气,起身走到旁边那个刚才说话的货郎跟前,掏出自己身上所有的钱,连同那26美元,塞进货郎手里。“麻烦你,”他指着地上的母亲,“帮她料理后事,剩下的,换点米面,隔三差五照应一下。”货郎愣住了,看看钱,又看看这个高鼻梁的外国人,重重点了点头。 之后几天,李敦白照常忙他的事,但心里总像坠着块石头。一周后,他鬼使神差又绕到那条巷子。黄昏时分,巷子很静,只有那户人家门口,摆着一小碗米饭,插着三炷细细的香,烟笔直地往上飘。货郎正从担子里拿出两个鸡蛋,轻轻放在门边。看见李敦白,他憨厚地笑了笑,没说话。 李敦白转身走了。他知道,26美元买不回一条命,也抚不平一道伤。但或许,它能变成几顿饱饭,变成邻居偶尔放在门边的一把菜,变成这个冰冷世道里,一点点不至于让人彻底绝望的温度。他抬头看看灰蒙蒙的天,想起自己远在加州的妹妹,也差不多这个年纪。风吹过来,有点凉,他拉紧了外套。 后来,李敦白因为工作要离开昆明。临走前,他又找到那个货郎,留了一小笔钱。货郎推辞,李敦白说:“不是赔命的钱。是请你,替那个再也不能回家的孩子,偶尔给她妈妈端碗热汤的钱。”货郎的手在空中停了停,最终接下了,用力握了握李敦白的手。 火车开动时,李敦白望着窗外飞逝的景物。他想,这世上有很多账是算不清的,但总得有人去做那道最简单的算术:一点善意,加上另一点善意,能不能让活下来的人,日子稍微好过那么一点点?他不知道答案。站台上,货郎的身影越来越小,终于看不见了。只有火车规律的哐当声,响在渐沉的暮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