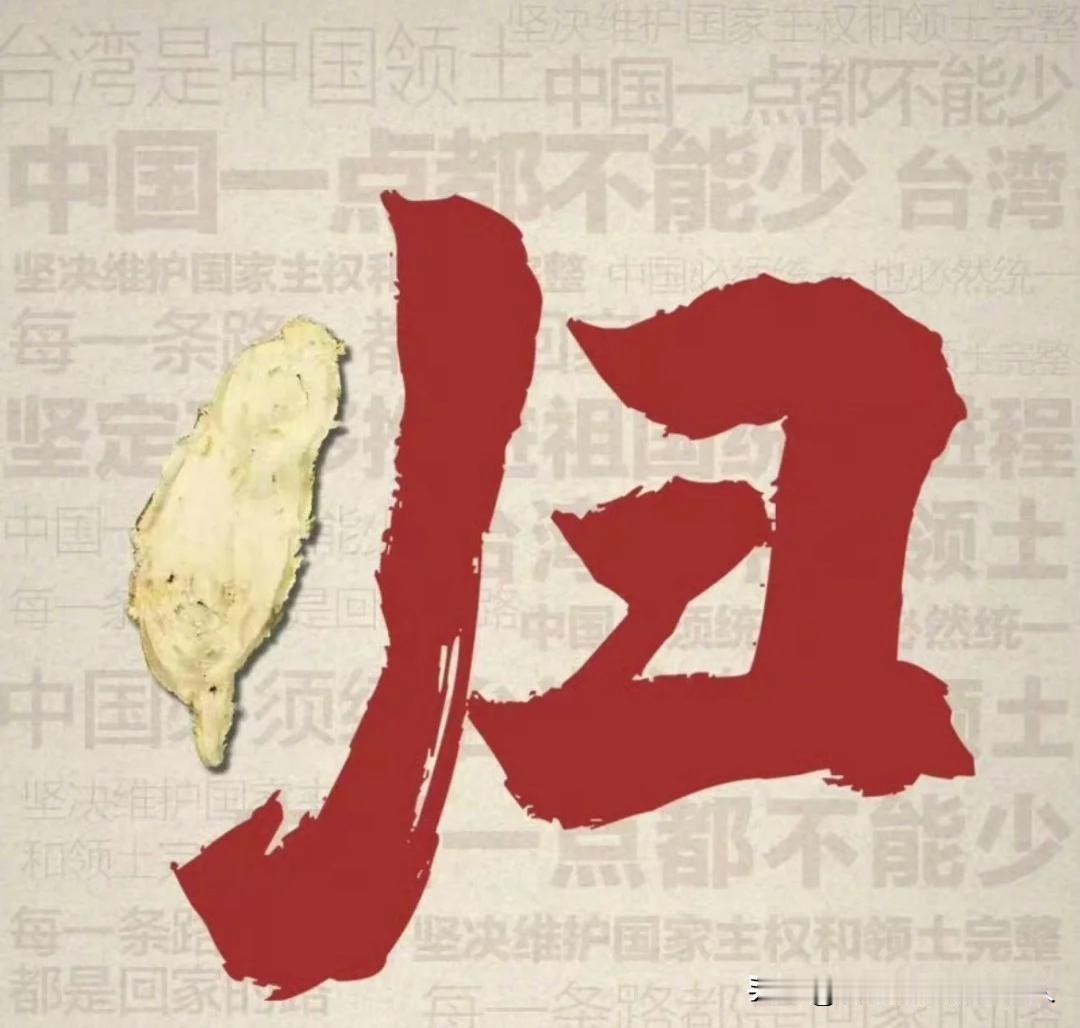辅警能否独立取证?
#律师来帮忙#
辅警在公安机关中协助警察开展警务,有协管员、文职等,对外统称“辅警”。他们虽名称带“警”并着非人民警察
#律师来帮忙#
辅警在公安机关中协助警察开展警务,有协管员、文职等,对外统称“辅警”。他们虽名称带“警”并着非人民警察制式服装,除个别地区享有事业编之外,大多隶属于劳务派遣公司,与公安机关并没有法律上的劳动关系。身份的错位使辅警在执法取证时主体资格面临法律障碍,按公私法主体分离原则,作为商务公司员工的辅警不具备行政主体资质,无法依法开展取证等行政行为,独立“取证”缺乏法理支撑。若辅警取证出错,公安机关与劳务公司责任划分不明,行政责任归属存疑。更关键的是,辅警取证动机偏向经济利益,缺乏“主体良心”及对法治精神与公共价值的认同,主体正当性饱受质疑。
从权力规则角度看,辅警取证存在法治缺陷。按理辅警应在民警带领下辅助执法,不具独立取证资格,但现实中常被安排独立取证,既缺乏法治自觉,也违背权力运行的基本规则。其行为未能体现“自由”这一权力原始约束力,未受“法律”这一权力亲生规则的支配,亦未获得合法“授权”这一“抱养”规则支持,更未严格遵循依法行政的程序要求。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和授权程序,辅警的取证行为事实上处于“无法”状态,容易构成违法取证,缺乏法律效力。辅警取证既脱离法治轨道,又违背权力制约原则,暴露出自由缺位、法律真空、授权失范、程序失控与违法风险等多重制度性问题。
辅警取证本应属于行政事实行为,服务于公共管理目的,但因辅警身份隶属于劳务派遣公司,其取证行为被商事因素深度渗透,令行政行为出现“商事异化”。在实践中,警务外包、警力外聘已成常态,辅警取证虽具行政外观,却以商事契约为基础,行政权被商业逻辑“染色”,偏离公法本质。传统行政权应依公法规则运行,而辅警取证却以商务公司运作方式介入,导致行政权的实质被商业化取代。同时,辅警缺乏依法取证的法治思维,使权力法定原则异化,行政权运行脱离法治轨道。辅警取证从行政行为演变为商事操作,不仅削弱了行政权的法治属性,也损害了公权力的权威。
辅警取证在主体身份、权力规则及商事化倾向上均存法律疑点,其程序运行同样缺乏正当性。程序本应是法治的核心保障和合法性的衡量标准,但辅警取证多以行政实用为导向,由在编民警决策、辅警执行,形成行政利益链条,缺乏法定程序与参与保障。在程序正当性上,辅警取证未体现程序公正与合法性导向,程序价值被行政效率取代,程序正义沦为形式。与此同时,辅警取证既无明确行政程序依据,也未体现行政自我治理理念,导致程序运行脱序、缺乏公正。辅警取证程序存在过程缺位、正当性不足、公正性缺失与行政程序缺乏等多重问题,反映出其程序层面法治规范的系统性失衡。
辅警取证在程序失范的基础上,其道德层面亦存在明显缺陷。道德作为非强制性行为规范,应体现诚信、良心、理性与正义等价值,但辅警取证背离了这些基本伦理标准。其行为缺乏政府诚信支撑,以经济利益为导向,削弱了公众对公共权力的信任。辅警并非法定公职人员,缺乏行政主体的道德良心基础,取证行为难具公共道德属性。其行为缺乏理性与正义标准,忽视法治与伦理的内在契合。作为权力行为的辅警取证未体现权力道德,应有的善良理性与公正精神缺位。辅警取证在诚信、良心、理性、正义及权力道德等方面均存在失衡,暴露出法治与道德脱节的深层问题。
辅警取证的效力价值存在多重缺陷,主要体现在平等性、合法性、合理性和职务性四个方面。作为劳务派遣人员,辅警主体地位不具行政平等性,难以与正式警察在法治结构中平等对应。其取证行为缺乏法律授权和程序依据,不符合法治标准,因而缺乏合法性效力。在未具合法基础的情况下,也无法形成科学、理性的合理性标准。由于辅警取证本质上源自商事领域,难以体现依法行政的职务本质,其行为既不具行政权威,也不具法治约束。辅警取证的效力体系失衡,无法满足法治与道德的双重要求,唯有通过完善立法赋权或彻底废止此类取证行为,方能维护依法行政与公权力的正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