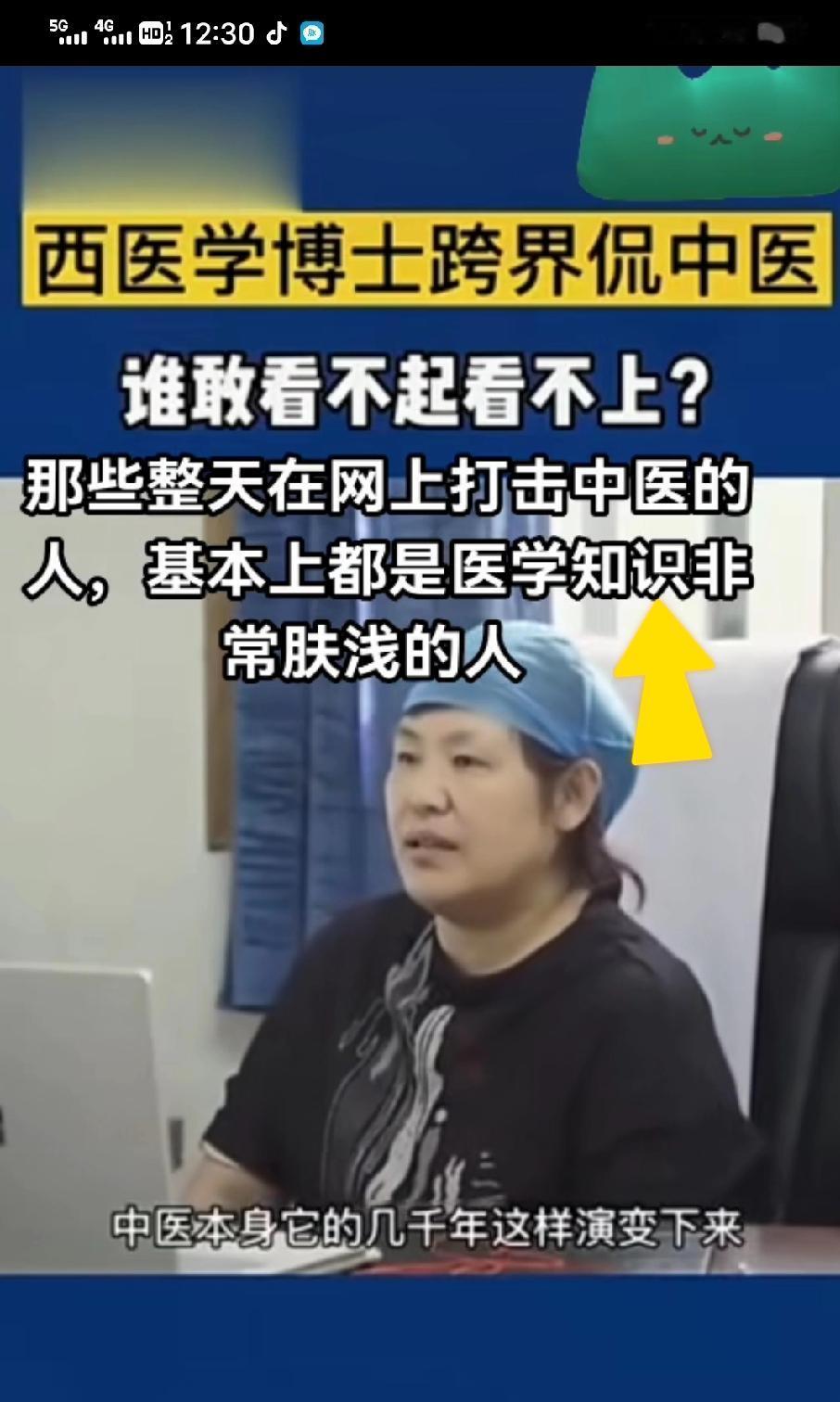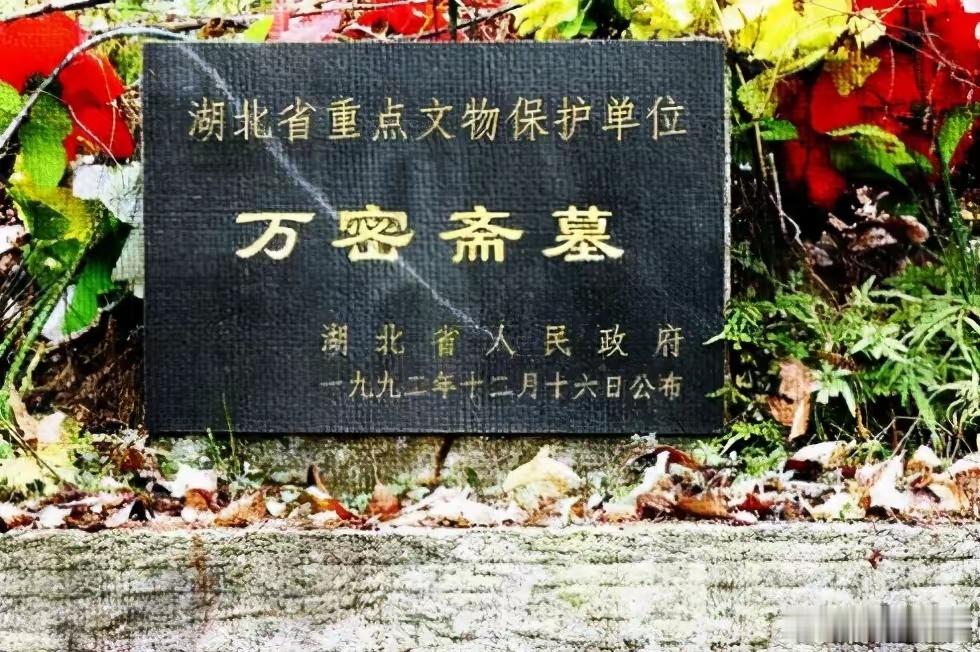四时用药原则。“春夏养阳,秋冬养阴”养生原则在指导四时用药方面,正如李时珍《本草纲目·四时用药例》所谓:“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秋月宜加酸凉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冬月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
春夏自然界阳气升浮,久病阳虚之人当于春夏之际借自然界阳气补机体不足之阳;秋冬阳气潜藏,阴虚之人可用酸苦寒凉之药补不足之阴,此即“顺时补之”,是因时制宜的体现。
因时制宜,用药注意补泻。另一方面,如《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曰:“司气以热,用热无犯;司气以寒,用寒无犯;司气以凉,用凉无犯;司气以温,用温无犯。”这是告诫医者用药勿犯四时寒热温凉之气,即春夏慎用温热药物,用热远热;秋冬慎用寒凉药物,用寒远寒,此即“逆时泻之”,同样是因时制宜的灵活运用。

那么,何时顺时补之,何时逆时泻之呢?纵观《黄帝内经》之论及后世医家之发微,可概括为“不足之病,顺时补之;有余之病,逆时泻之”两句话。下面分以四时阐述之。
春为阴中之阳,少阳,肝应春,其性主生发上升
若春时肝生发不及,则应促其生发之性以求天人相应而和,用药方面即如李时珍《本草纲目·四时用药例》所谓:“春月宜加辛温之药,薄荷、荆芥之类,以顺春升之气。”顺其性为补,反其性为泻,故不及者应顺之。
《黄帝内经》云:“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以辛补之。”又曰:“肝胆温补凉泻,辛补酸泻。”反之,若肝气本有余或肝阳素亢,或逢春时令生发太过,此时若再投辛温之药则犹抱薪救火,对此则应逆之泻之,“亢则害,承乃制”,故当“以酸泻之,以凉泻之”。
夏为阳中之阳,太阳,夏气通于心
此时阳盛于外而虚于内,若心不应时难以升浮阳气或心阳本有不足则为不及,易生寒,此“逆夏气则太阳不长,心气内洞”。此时应顺其性而养之,正如李时珍所谓:“夏月宜加辛热之药,香薷、生姜之类,以顺夏浮之气。”

见之临床,其机体阳虚内寒而生咳喘、泄泻之病,遇冬、遇寒则犯,可在夏季阳气充盛之时以辛热药或温灸之法补不足之阳,此即“冬病夏治”之意;反之,若心阳升浮太过则为心气有余,可见邪热炽盛之证,当遵《黄帝内经》“热淫于内,治以咸寒,佐以甘苦”之意逆时泻之。
土居中化,在时为长夏,在人之脏为脾胃
长夏为万物所化之时,《周易·系辞下》云:“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故万物之生化关键在天地之氤氲,即天气下降、地气上升相交之势。
若脾胃升降无权或因时升降不利,则阳不得降、阴不得升而成痞,治疗当参李时珍所谓“长夏宜加甘苦辛温之药,人参、白术、苍术、黄柏之类,以顺化成之气。”《伤寒论》所载辛升苦降之半夏泻心汤类即为调其升降而设。
秋为阳中之阴,少阴,秋气通于肺
若秋时人不与天地相应,应降不降,在胃家可有阳明经热证、阳明腑实证,仲景白虎汤、三承气汤即为胃降不及而设;若为肺降不及,《黄帝内经》谓:“逆秋气则太阴不收,肺气焦满。”而致肺热叶焦胸中胀满之证,治疗当遵《黄帝内经》所载“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以酸补之”、“肺大肠凉补温泻,酸补辛泻”。李时珍云:“秋月宜加酸凉之药,芍药、乌梅之类,以顺秋降之气。”
但若肺降太过,亦可为病。如《黄帝内经》曰:“肺苦气逆,急食苦以泄之,以辛泻之。”以辛泻之,即取辛温升散以防肺降太过,如吴鞠通杏苏散,即“逆时泻之”之类。

冬为阴中之阴,太阴,冬主沉藏,在脏应肾
藏者为阳气潜降藏于下焦以奉阴精,若冬时肾沉藏不及,则“宜加苦寒之药,黄芩、知母之类,以顺冬沉之气”、“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以苦补之”。若冬令沉藏不及而生虚热,则取六味地黄丸、知柏地黄丸促其沉藏,此“顺时补之”之类。
然冬令进补远非苦寒滋阴一途,阳气不足之人,冬季尤当慎用苦寒之品以免伤阳,即“用寒远寒”,否则肾因过寒而水凝,水汽不腾化为燥象。此时之补,当遵《黄帝内经》中“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以辛散之药散凝寒之弊,而水汽上蒸肾燥自解。仲景当归生姜羊肉汤千年不衰,成为阳虚之人冬令进补之良方,如四逆汤、真武汤辛热回阳更为医家所习用。此“阳生阴长”之理,亦为因人、因时制宜之灵活运用。
三因(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四时健康
综上所述,“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是《黄帝内经》养生保健、防治疾病的指导思想,体现了“天人相应”的整体观念,对指导预防治疗有重要的意义。
但临证用药时不可一概理解为“春夏补阳、秋冬补阴”,当因人、因时、因地制宜,首辨机体阴阳气血之盛衰,再参合时令,以药物五味之偏,纠正机体阴阳气血之偏盛偏衰,即“不足之病,顺时补之;有余之病,逆时泻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