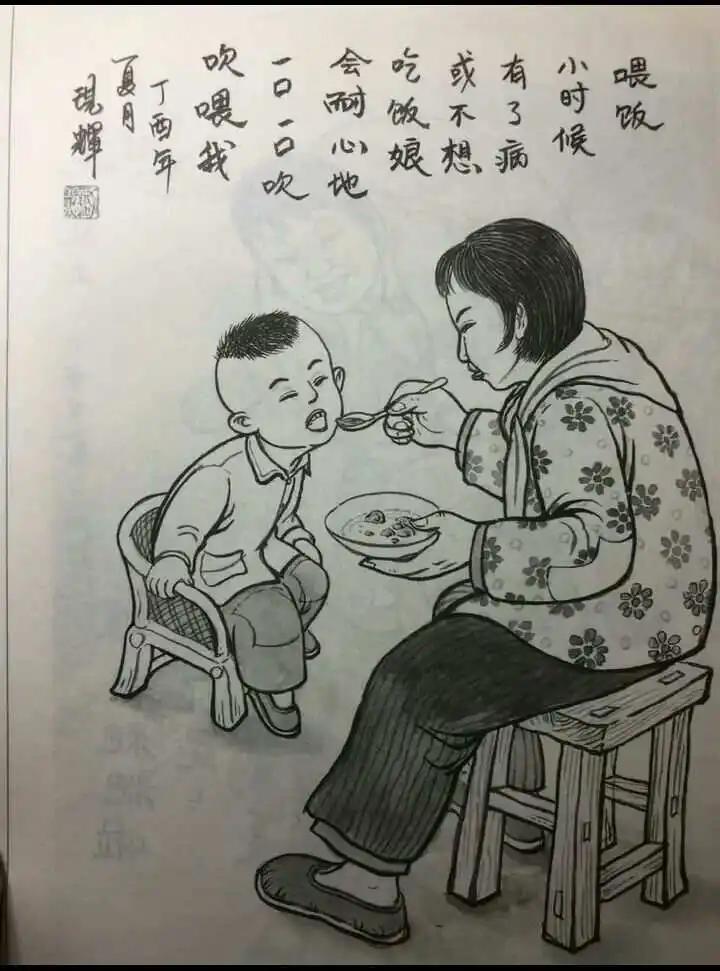故乡记事·人物记·26·游街的妇人 我十来岁儿的时候儿,庄里没啥娱乐,一年除了大队放几场电影儿,界壁邻右婆婆媳妇儿、两口子打架,父母追着一边儿跑一边儿犟嘴的半大小子打骂就是个乐子。除此而外,上演最多的“娱乐”项目儿,也许就是“游街”。 那时候儿游街的事儿挺多。国家、县里、公社儿、大队有需要,把“四类分子”拎出来游一圈儿,由武装民兵押着,有时候儿民兵一边儿走一边儿喊口号儿,语气激烈,“四类分子”却一声不吱,耷拉着脑袋,面无表情地走着;有时候儿逮住偷摸队里粮食、饲料甚至偷着从地里拾一点儿柴禾的人,也可能游一游。有一年过年前几天,梁泡儿有一群人“干儿牌”(方言,打扑克)赌钱,挨公社儿抓住,也挨公社儿的公安助理和大队的民兵押着,从梁泡儿过于家泡、姜泡儿,一直游到姜泡儿庄东头儿的公社儿大院儿,惹得几个庄儿庄筒子都挤满了人看——因为挨抓的“赌博犯儿”爱分辨说,“打个一毛两毛的百分儿,就是磨磨手牙子,消磨时间”,所以不管“五冬历夏”,只要抓住赌钱的,带到公社儿,都要让他们面朝墙站一排,高举双手在墙上上下蹭,“让他们过磨手牙子的瘾”。寒冬腊月儿,这些人将要面临这么有趣儿的处罚,而且说不定有身边儿哪家的亲戚,甚至哪家姑娘没结婚的对象,哪不想看看? 在游街的人里,给我留下印象最深、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刘旮旯儿一位妇人。那是一个夏天,麦收的时候儿,我在庄里小学上三四年级,这妇人忽然来到学校面朝北的大门前小广场儿上,胸前挂着一把儿、身后背着一小捆儿麦子,手里敲着一面小铜锣儿,敲几声儿停下,就低着头儿小声儿叨叨:“我是三队的 x x 家,我偷队里的麦子来着,大伙儿都别跟我学!”(学,方言读作“消”)再敲,再叨叨。 很快,妇人的身边儿围满了小学生,她既不躲闪逃走,也不抬眼看围着她叽叽喳喳议论或看够了径自在一边儿玩儿耍的我们,只是接长不短儿地敲几下儿锣,低唤几声:“我是三队的 x x 家,我偷队里的麦子来着,大伙儿都别跟我学!”奇怪的是,她身边儿并没有人监督管理,但敲锣、低唤,却一直没有间断。 不久,上课的钟声悠悠响起,我跟同学们丢下她,跑向教室。奔跑中我回头儿看一眼,妇人还在那儿呆呆木木地站着。等下了课,小广场儿上却已空无一人,也许她又“游”到别的人多的地方儿去了吧。 高泡儿大队庄大,由6个自然村儿组成,虽然说起来是一个大队的,我却不认得这个妇人。她家在庄东头儿,我们家儿在庄西头儿,得界有一里多地,又不是啥亲戚,不认得很正常。那么,她们家儿很穷吗? 一个老娘儿们儿,为啥偷麦子?这在从小儿受到严格的“打死也不兴偷啥儿”、“姑娘媳妇儿更不兴黏手黏脚儿,让人家笑话”教育的我看来,真是不可思议;大队让她游街,又是啥意思?当时“搞社儿”已经到了“末秋年”,除非有“外来项儿”,指着从队里分粮食、柴禾,根本不够吃、不够烧,社儿员从地里、场里偷生产队的粮食、柴禾已然成风,为啥非得逮住她,让她一个老娘儿们儿在大日头底下游街? 后来长大一点儿,我听到了一些关于这个妇人不好听的传言,人们说就是因为这个,大队看轻看贱她,觉着她“没脸不害臊”,逮住她让她游街,她也不觉着丢人,更不会寻死觅活,才让“看青的”在数不尽的偷啥儿的人里专门儿逮住她,让她游街,做“反面儿典型”,教育大伙儿别偷队里的东西。 这妇人若现在还活着,大概也得有七十多岁、儿孙成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