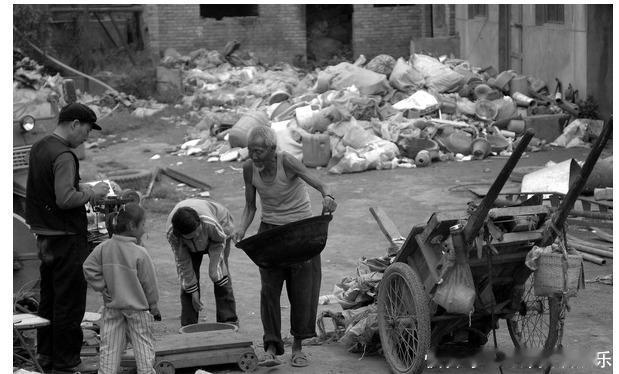故乡记事·人物记·45·小买卖三老儿之三·“大爷”(上) “大爷”是于家泡老李家我的祖父辈儿人,家里兄弟两个,他是老大,我们尊称他为“大爷”。 提起大爷,我就会想起张炜的长篇小说儿《古船》里“隋不召”这个人物儿。他们说话同样的“不着调”,做事儿同样的不羁,同样的“不治生业”,却同样的富有同情心和助危扶困的义气,在生前,同样地得不到身边儿人们的认可。只是书里的隋不召瘦小,大爷却身材中等,显得更精壮一些。 大爷年轻的时候儿,赶着马车拉着老李家“大老太爷”、举人“润老爷”的孙子、他一位五六岁儿的叔伯兄弟上滦县县城看亲(方言,探亲)。走到半道儿,经过一片花生地。于家泡所在的“泡里”地势低洼,土是黏性黑土,不适合合种花生,大老太爷的孙子从小儿没看见过花生秧子,问大爷是啥,大爷说:“这就是落花生啊!咱们拔它几把吃。”说着吆喝住牲口,跳下车辕子,快跑着上地里拔了几撮花生,扔儿车厢里,一边儿继续赶着车走边儿跟孩子一对一嘴儿地吃起来。 车没走出多远,就被人追上。追的人气喘吁吁地怒问:“你们是干啥的?好模样儿(方言,没事,没缘由地;样读三声)拔落花生做啥?” 大爷赶忙解释:“我们上滦县看亲去,孩子没看着过落花生,我就给他拔了两把。咋的咧?” “咋的咧?知不道不让拔落花生啊?要是你家的,你让哪随便儿拔呀?!走,跟我上“会上’去,非罚你点儿钱不可!” “会上”,是人们对当时庄里的管理机构“联庄会”或“维持会”的俗称,“联庄会”或“维持会”的掌事儿人叫“会头”。大爷说:“大哥你看就吃这么俩落花生,还是给孩子拔的,你也别生气,就算咧吧。” 追的人不干,非让上庄里。大爷赶上车,追的人在后头跟着,到了“会上”。 “会头”们正拉嗑儿,追的人说:“逮住偷落花生的了,拔儿我们好几撮落花生,得罚他钱呐!” “会头”们围上来,问大爷因为啥拔落花生,是哪庄儿的,有的恶声丧语地吵吵:“是得罚钱,说咧不让拔还拔!”“你是哪庄儿的,干啥去?” 大爷一看,并不着急,反而慢声拉语儿地说:“你们可别吵吵,吓着我们小少爷儿可了不得。” 人们一下儿肃静下来:“小少爷儿?咋回事儿?说说!” 大爷说:“这是于家泡‘润老爷’的孙子,一早下让我拉着上滦县看亲去,小孩子儿没看着过花生秧子,我也是,寻思给他看个新鲜儿,就拔了几撮,还值得这样儿?这要给孩子吓出个好歹儿来咋整?” “会头”们一听:“于家泡润老爷的孙子?真的假的?” “那还有假!我叫 xxx,我管润老叫大爷,这是他孙子,小名儿叫 xx。我们上滦县就是我大爷叫我带着他看我姑去。” 大爷说完,“会头”们互相看看,马上变了笑脸儿:“哎呀,那还说啥?你咋不早说?这么大儿个孩子,吃俩落花生算啥?”其中一个人扭头儿跟庄里人说:“去,再给孩子拔两撮去,拿着道儿上吃!润老爷的孙子吃咱们两棵落花生,还不是看着咱们了呀?!” 庄里人拔儿来一大抱落花生,恭恭敬敬地把大爷哥儿俩送出庄,“会头”们临出庄还嘱咐:“兄弟你可得把孩子看好溜,别颠着啥的!”大爷一边儿说着感谢的话儿,一边儿上了路。 我爷会我二爷年轻的时候儿,跟大爷一起儿上倴城赶集卖粮食。粮食卖了,哥儿俩说回家,大爷撺掇俩兄弟上“赌局子”去赌钱,说“赢俩钱儿再家去。”哥儿俩架不住劝,跟大爷来到“赌局子”“着宝”,即赌牌九不一会儿,俩人卖粮食的钱都输了。 我二爷爱财如命,又怕回家交不了差,非跟人家要回来,人家不给,就说人家“作假”,骗钱。开“赌局子”的是啥人?不是街上的“无皮虎儿”,就是跟“警局子”勾着,哪儿吃这个?上来几个人就要打二爷。 大爷一看,赶紧喊:“大伙儿先别打,我这回就上南关儿学校找校长去,让他叔把他们带走!”说完扭头儿做出要去找人的样子。 人们一听,拉住大爷问:“校长?哪个校长?” “就是李荣周荣老爷呀!” 那时候儿已经是民国,老李家进士“二老太爷”联合其他几位绅士,拆了倴城寿圣寺西南边儿的“老母庙”,建立了倴城一带第一所儿新式儿小学,二老太爷当校长。校长虽然不是啥官儿,但有着进士、校长双重身份的二老太爷,在社会上却忒有地位。“赌局子”的人们听了这话,停止了吵骂,打听清楚大爷说的确实不是假话,把钱还给我爷会二爷哥儿俩,还多给了一点儿,放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