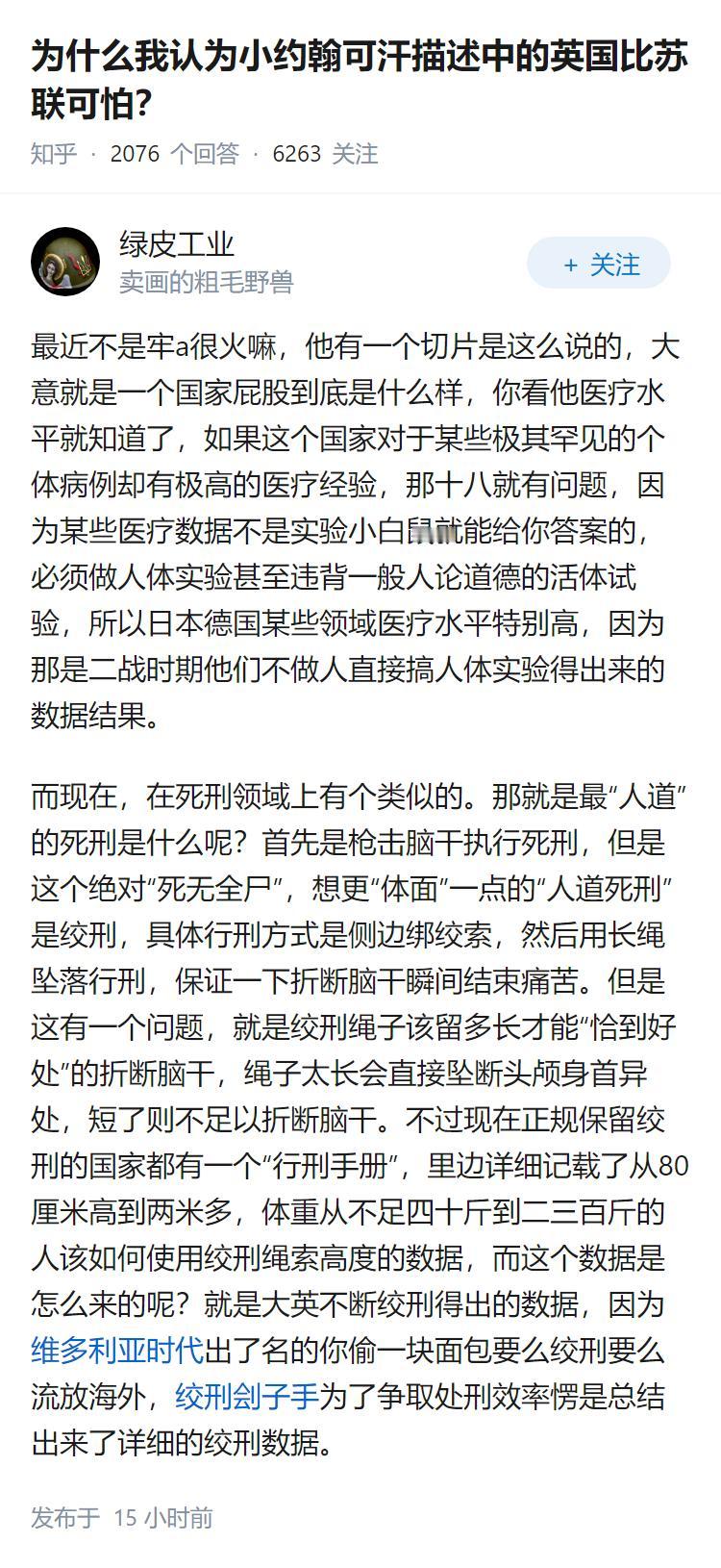苏衍霈,这名字大家可能不熟。她是一位来自中国的无国界医生助产士。
在这个大家都恨不得离中东火药桶越远越好的时候,她今年7月第二次逆行回到了加沙。35岁,本该是享受生活的年纪,她却把自己扔进了全世界最凶险的地方。
她在纳赛尔医院的伤口处理部门只待了30分钟,就崩溃了。
当我看到苏衍霈的描述时,我依然感到一种生理上的不适。送进来的全是不到半岁的婴儿,全身烧伤,或者被弹片划开的恐怖创口。医生揭开绷带的时候,孩子们疼得撕心裂肺。
那种哭声,不是我们在商场里听到的孩子撒娇,那是生命本能的、绝望的尖叫。
苏衍霈哭着问:“为什么,这个世界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无辜的孩子身上?”

这也是我想问的。如果所谓的“完成任务”和“自卫”,必须以把半岁的婴儿送上手术台(甚至因为物资短缺只能切开气管)为代价,那这种“正义”的含金量,是不是太低了点?
在医院里,除了血腥,还有一种更折磨人的东西——饥饿。
这不是我们平时说的“饿了一顿没吃饭”,而是真正意义上的“饥荒”。苏衍霈发现,曾经并肩作战的当地同事,每个人都瘦脱了相。他们脑子里没有工作,没有未来,只剩下一个念头:全家三天只有一个面包,我到底吃不吃?
想一想,如果是你,你怎么选?你吃一口,孩子就少吃一口。

苏衍霈自己也倒下了。每天一顿饭,连续两周的极度饥饿让她患上了严重的肠胃炎,不停地呕吐。在加沙,活下去已经不再是一种权利,而是一种侥幸。 营养中心只有9张病床,却要塞进20个病人,床位使用率高达300%。那些皮包骨头的孩子,有些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救了。苏衍霈说得很直白:“纯粹是饿死的。”
而在几公里外,以色列军队认为排队领救济粮的人群“不守规矩”,于是开火。为了抢一口吃的被打死,这就是加沙的常态。

在这场战争里,消失的不仅仅是建筑,还有那些鲜活的人和原本触手可及的未来。
苏衍霈提到过一个十岁的小男孩。他在纳赛尔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全身缠满绷带。他的妈妈是医院的员工,在轰炸中腿断了,只能坐轮椅。
苏衍霈记得那个男孩的眼睛,曾经特别明亮,透着那个年纪特有的机灵劲儿。但在呼吸机的起伏中,这双眼睛最终还是闭上了。他走了,成为了那6.6万名死亡名单中一个冰冷的“1”。 他的妈妈依旧坐在轮椅上,面对着废墟和回忆。
这种故事每天都在上演。

还有一个叫阿萨夫的学者,家里曾经有3万册藏书。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书就是命。但现在,家没了,书烧了,他带着全家挤在帐篷里。为了煮饭,他不得不花高价买木柴;为了给大儿子凑毕业费,他卖掉了妻子的首饰。
最让他绝望的,是看着自己的孩子在废墟中变得麻木。三儿子连续两年没法参加高中毕业考,小儿子变得对周围的一切漠不关心。阿萨夫说:“加沙整整一代年轻人都被毁了。”
这话说得太重,也太真。教育、礼仪、梦想,这些构建文明社会的基石,在两年的炮火中被炸得粉碎。当一个孩子不再关心明天,不再有礼貌,只知道躲避炸弹和抢夺食物时,这才是最彻底的毁灭。
还有那些“流离失所”的人。这四个字听起来很书面,实际上就是一场没有终点的逃亡。

穆罕默德阿尔蒂比,看着以军空投的传单,心里一片冰凉。这种传单他见过太多次了,每次都说“去南方吧,那里安全”。结果呢?他们去了拉法,去了努赛拉特,发现所谓的“安全区”不过是另一个屠宰场。
“如果我现在离开家,我将会流落街头。” 这是一个成年男人最无助的时刻。

在这场战争中,有一群人特别值得我们致敬,那就是坚持在现场的记者。
以色列自开战以来,基本禁止了国际记者独立进入加沙。我们能看到的一手画面,全靠当地的巴勒斯坦记者拿命在换。
玛丽亚姆阿布达卡,33岁,一位母亲,也是一名记者。她曾把自己的一个肾脏捐给了父亲,是个极其孝顺、坚韧的女性。然而,四个月前,她的母亲因为缺乏治疗,死于癌症。这就是加沙的医疗现状:不仅救不了伤员,连常规病人也只能等死。
8月25日,当我们在空调房里刷着手机时,玛丽亚姆背着摄影机,在纳赛尔医院外记录病人撤离。

一声巨响,她倒下了。
那天,以色列军队对医院的打击造成了20人死亡。内塔尼亚胡事后说这是“悲剧性的意外”。一句“意外”,轻飘飘地带走了一条鲜活的生命,留下她13岁的儿子盖斯在这个世界上孤苦无依。
苏衍霈哭了。她在医院里的很多照片,都是玛丽亚姆帮忙拍的。
第二天,苏衍霈问同事:这么危险,还要让记者来吗?同事们的回答让我肃然起敬:“如果没有他们,世界就看不到这里的真实处境,可能连食物援助都不会来。记者和医护人员一样,不畏惧死亡,都想为世界见证这里发生的悲剧。”
正是因为有了玛丽亚姆这样的人,我们才得以窥见真相的一角。社交媒体把加沙的苦难怼到了全世界的脸上,让人无处可躲。

说实话,这两年,国际社会的反应让人心寒。
那个巴勒斯坦非政府组织网络的阿姆贾德沙瓦,一位55岁的老人,他说了一句大实话:“国际社会从战争一开始就失败了。”

早在2024年初,国际法院就提到了种族灭绝的风险,结果呢?无视。彻彻底底的无视。
直到今年9月,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终于认定以色列在加沙犯下“种族灭绝”罪行。紧接着,英国、法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西方国家,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继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建国。
这算什么?良心发现?还是形势所迫?

我看更多的是一种地缘政治的止损。 9月26日联大会议上那空荡荡的会场,已经说明了问题。以色列的一意孤行,连它的盟友都觉得“带不动”了。那个所谓的“正义”大旗,已经破得连遮羞布的作用都起不到了。
美国呢?白宫在9月底公布了特朗普的“20点计划”。以色列表示支持,哈马斯和以色列代表团也开始在沙姆沙伊赫谈了。八国外长发声明欢迎。
表面看,好像和平的曙光来了。
但我们别忘了,在这之前有多少次停火协议变成了废纸?沙瓦老人说得好:“人们不能靠声明充饥。” 外交动作必须转化为地面上的实际行动。只要以色列的军队还在医院里开火,只要那个叫“E1区”的定居点还在扩建,只要美国的武器还在源源不断地运送,这种“和平”就极其脆弱。
我们要清醒地看到,美国依然在用否决权“庇护”以色列,依然试图通过以色列来掌控中东的安全秩序。哪怕是现在这个看似积极的停火谈判,背后依然是大国之间赤裸裸的利益交换。

写到这里,心情很沉重。但我也看到了一些不一样的东西。
那就是——韧性。
苏衍霈在任务结束的时候,选择了留下。她申请延长任务期到10月份。她说:“现在是非常关键的时刻,我想留下来。”

沙瓦,那位看透了政治虚伪的老人,依然没有放弃希望。他的动力来自那些孩子——那些在废墟上努力学习、帮家里找水的孩子。
还有那些失去了一切的妇女,她们在岩石上、平原上重新挖掘,搭起一个临时的家。
“我们不是被记录的数字,而是生命、梦想、未来和权利。”
这句话,应该被刻在联合国大厅的墙上。

加沙的这两年,是一面照妖镜。它照出了霸权主义的丑陋,照出了国际机制的无力,但也照出了人性中最顽强的光辉。
我们在相信什么样的正义?

也许,我们不能再相信那种挂在嘴边的、写在文件里的“正义”。那种正义太远,太虚伪。
我们能相信的,是苏衍霈留下的背影,是玛丽亚姆倒下前紧握的摄像机,是那位在废墟中给孩子讲故事的父亲。
这种正义,虽然微弱,虽然带着血泪,但它是真实的。它在告诉全世界:你可以摧毁建筑,可以切断粮食,但你无法从内部让一个民族自我遗忘。